Shao Zhou Li
Li Shaozhou, was born in Luoyang in May 1956, and joined the army in 1976. From 1985 to 1987 he studied the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Art Department of the PLA Art College, then became a professional painter at the art office of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2nd Artillary Force. He i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rtist Association, a councilor of the Beijing Delicate Painting Association. In 1980, Mr.Li published his first painting, from then on he often takes part in important art exhibitions of the army or the country, and some of his works were collected by the Chinese Art Museum and gained award. He forms his own distinctive art style.
Discover contemporary artworks by Shao Zhou Li, browse recent artworks and buy online. Categories: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ists. Artistic domains: Painting. Account type: Artist , member since 2007 (Country of origin China). Buy Shao Zhou Li's latest works on ArtMajeur: Discover great art by contemporary artist Shao Zhou Li. Browse artworks, buy original art or high end prints.

Artist Value, Biography, Artist's studio:
Recognition
Biography
Li Shaozhou, was born in Luoyang in May 1956, and joined the army in 1976. From 1985 to 1987 he studied the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Art Department of the PLA Art College, then became a professional painter at the art office of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2nd Artillary Force. He i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rtist Association, a councilor of the Beijing Delicate Painting Association. In 1980, Mr.Li published his first painting, from then on he often takes part in important art exhibitions of the army or the country, and some of his works were collected by the Chinese Art Museum and gained award. He forms his own distinctive art style.
-
Nationality:
CHINA

- Date of birth : unknown date
- Artistic domains:
- Groups: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ists
Ongoing and Upcoming art events
Influences
Education
Artist value certified
Achievements
Activity on ArtMajeur
Latest News
All the latest news from contemporary artist Shao Zhou Li
Article
Li Shaozhou, was born in Luoyang in May 1956, and joined the army in 1976. From 1985 to 1987 he studied the chinese painting in the Art Department of the PLA Art College, then became a professional painter at the art office of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2nd Artillary Force. He is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rtist Association, a councilor of the Beijing Delicate Painting Association. In 1980, Mr.Li published his first painting, from then on he often takes part in important art exhibitions of the army or the country, and some of his works were collected by the Chinese Art Museum and gained award. He forms his own distinctive art style.

Article
采撷心灵之花
我平时苦心经营且数量也最多的是现代人物画,以藏族人物为重点,还画北方农村人物和傣族人物,当然职务所在,也要画军旅人物。人物画严谨的造型、复杂的构成、深邃的内涵,一直让我痴迷陶醉,也常常令我困惑痛苦。万般滋味,三五句难以言表。
其实人生和自然给我们心灵的感受、感动、感悟是很繁杂零乱的,许多时候觉得人物画难以全部承载和恰当表达,我就将其寄寓在花草树石之上,于是陆陆续续就做了一些不易按传统习惯归类的杂画。或画春草袅袅摇风,或绘夏荷亭亭玉立,或写一派灿烂之秋叶,或染一丸温暖之冬日。路边水畔,墙头瓦上,平凡场所,寻常之物,只要与之神交意会,都能引起我心灵颤动,化作一帧帧丹青。作这些画比作人物画轻松自由,欲红欲绿,任黑任白,自出心底,无所拘束,不必画素描作草稿改来改去,苦苦思索,而是拈毫随意勾勒点染,尽得绘画之快乐。一花一世界,一石一乾坤,作品理当有所寄寓,不能只是物象表面的描绘,然而也不必用心太深,绘画毕竟不是哲学图解,画者真心所作自然真情洋溢,观者若情有所动,心有所思,产生良性互动,也算不枉画者一番劳作了。作品的内涵,本来就是靠观者来解读、阐释、拓展的。
在体验绘画快乐的同时,我愈觉自己才疏学浅、心灵迟钝,不能深切感知人生和自然之万一,亦手法笨拙,不能把心灵的感知表达的深切精到。噫嘻!只能说不求尽善尽美,唯求尽心尽力吧。
寒窗苦学多困惑,万丈豪情几消磨。
拈取心底零乱事,写作春山与秋波。
(《名家名画·李绍周》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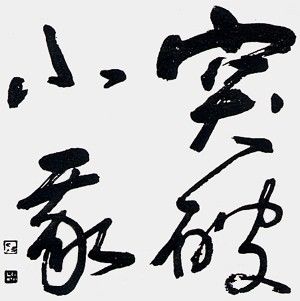
Article
作人物画,草稿阶段最难,要仔细推敲构图,构图千差万别,意境就大不相同了。其实此时的意境只有画者才能想象到,别人看到的只是一些粗糙的铅笔线架构而已。构图既定,人物造型又颇费脑筋。尽管有一些照片和写生可作参考,但一般而言,除了保留最动人的姿态,完全照抄是不可能的。
我的铅笔稿相对比较粗略,人物大的动态衣纹走向差不多就行,不必细抠。铅笔拷贝时,勾墨线时,都有一些变动和修正,这些变动和修正类似于画水墨画时的随机生发,不至于把工笔画弄成一个机械操作过程了。我往往在人物画得差不多时才酌情加上道具、环境等,使画面完整。
在画画的过程中,我有时气壮如牛,有时胆小如鼠,有时信心十足,有时灰心丧气。有时感觉如乘风破浪,有时感觉象骑虎难下。把人生感受、思想感情变为作品,特别是人物画,那绝不是轻松自在的,一幅好的人物画,构思与构图的结合,造型与个性的结合,色彩与情绪的结合,都要力求融洽和谐,表情达意准确,要思来想去,改来改去,一画完成,身心为之张弛数度,个中滋味,难与人言说。
画面是否成立,关键在于黑白灰三色之比例关系,比例恰当,主次分明,才能出现动人的效果。优秀的黑白版画和书法作品都能给我们以有益启示。黑白灰关系不当,画面或灰而无神,或花而凌乱,或浊而沉闷。
状物是一种层次,学画要达到得心应手,状物象形也不容易。写心是另一种层次,高于状物,写画者之心,手下万物只是画者情绪、思想、感情的载体,每作一画,多有寄寓,此所谓艺术家也。只精状物,不能写心,还只能说是手艺精湛而已。
心里有什么就画什么,心里没有就不要强画。用自己的嘴说别人的话是很痛苦或很无聊的事。有了某种感受,就要寻找一种适合它的形式,以求表现得充分、强烈。有时候也会先有一种形式感在心里,觉得很美,再去寻找适合它的题材内容。不论先有内容还是先有形式,只要两者能完美结合就行。象作诗,有时是有了中间的一两句,觉得不坏,再前后连缀构思成篇的。
在工笔画的绘制过程中,要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能贪快,否则就会粗糙或脏乱了。激情是很重要的,没有激情就没有了绘画的生命,但要把握好,不使其成为脱缰野马。工笔画是稳健的艺术,要稳健操作,不过不是机械冷漠的操作。就象驾驶一部动力强大性能良好的汽车去赴一个美丽的约会,要能控制住情绪,把好方向盘,不能太莽撞,否则很可能逞一时之兴,结局却并不美丽。
绘画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出错又不断改错的过程,不能怕出错,错误有时会告诉我们一些特殊的效果和技法,有时又可能引导我们去发现一个奇异的境界,而这种种好处是在按步就班、步步正确的情况下不可能得到的。
材料的变化,会给视觉带来新的感受,但材料就是材料,并不是艺术,艺术还要从艺术家的心里流出来才行。不重视材料不行,过于夸大材料的作用也没必要。真正的好诗无论是写在纸烟盒上还是印在精美的书上都是好的。真正高明的画家画在粗糙纸上的画也能穿越时空打动后人。任何一种材料和画法,都有其独特的效果,只要作者将其优点发挥到极致,就能产生独有的韵味。
物象愈单纯,意境愈突出。有时多不如少,有时少不如多,多多少少,视表现需要而定。画面要有实有虚,无实则流于粗疏空洞,无虚则病在词拙意浅。意境往往产生于虚处,就象诗词的意境往往出自于含蓄之处。当然,虚因实生,实因虚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我喜欢在整体中求变化,不能琐碎了,那样易流于零乱,导致小气。整体感始终是一幅画成功与否的关键一环。构图要有整体形式,强调张力,色彩应该和谐丰富,多种颜色叠染是好办法,可以使色彩厚实、复杂,避免单薄、单调。一幅画要染、洗结合,交叉使用数遍,洗掉浮色,使色彩看上去厚实,也可以洗出一些特殊效果。
有诗心才有诗情,以这样的心情去看生活,自然能体味到其中的诗意。构图关乎意境,虚实关乎气韵,色彩关乎情调,三者之间也有交叠互补。
好画不论大小。大画应大气中求精到,远观有气势,近看有韵味,不失于粗糙纷乱;小画应精到中求大气,细致而整体,丰富而单纯,不失于拘谨琐碎。能顾此两端,方为丹青高手。
作画用好加法不易,用好减法更难,需要更透彻敏锐的思想和更含蓄精湛的技艺。唯其如此,方能真正抵近中国画“写意”的精神内核。当然艺术没有定法,任何一条道路都有可能臻于上境,修成正果,方法并无高下之分,艺术的高下区别只在于作品传达给读者的气象是雄浑开阔还是琐碎渺小,意境是深邃隽永还是苍白枯燥,情感是真诚质朴还是矫揉造作,趣味是清新高雅还是混浊低俗。
作画不易,说画更难。我可以把自己漫无边际的情思连缀经营成一幅幅画,奉献给读者,但我无法用语言和文字确切地说明它。因为它是我心血情愫的凝结聚合而不是某种观念的诠释图解。非要说出来,首先自己就觉得索然无味了。再说读者绝不比作者笨,作品一经面世,大家自会品味甘苦,分辨良莠,作者若再对自己的作品条分缕析,那就是画蛇添足了。
创作初时,我东奔西走,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之林里寻觅喜爱的素材,苦思冥想,忽然灵光一闪,偶有所得,我将那一闪灵光反复咀嚼再三品咂,把握其内涵,然后在无数草图推敲中渐渐有形。好像已经满意,但一觉醒来再看又觉词不达意,遂断然毁之;又陷入苦思。数次来回,终于定稿。这就象在大自然中虔诚地汲取日精月华,天地好合,蓦然受孕。
草图能够表达构思后,就开始进入正式作品制作。此间正象胚胎在母体中缓缓发育,作品中人物的五官四肢,姿态情绪,山川的走势流向,雪雨晴风,花鸟的枝叶翎毛、荣枯动静,都慢慢地显现出来,画面开始有了生气。这时候要保持住灵光一闪时的激情和新鲜感受,更要克制住急于求成的浮躁,用母亲般的耐心和沉稳,细心甚至是苛刻地调整充实画画,使之平衡、和谐、不断完善。距离产生美,新鲜产生美。城里的人常年生活在高楼大厦间,只觉其拥挤堵塞,空气污秽;山里人常年生活在峻岭大石间只觉其寂寞冷清,单调乏味,都不觉其美了。互相换看一下,美感又出现在眼睛里了。
画画时心里是踏实的,满眼只是线条和色彩,心里空空的又满满的,很平淡也很快乐。一幅画完成后,往往落入莫名的迷惘和烦闷之中,再作新画时,方才拂去迷惘和烦闷,重得平淡和快乐。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了我的一生。
想画画而脑子里没有形成画面时,就像想要孩子可还没有怀胎的女人一样,我的情绪是期待又迷茫,焦躁而空虚。(李绍周)
我的画,是我在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上艰难跋涉的一行蹒跚足迹;是我从军以来对这世界体察和理解的一页心得;是我心田流淌出的一支无名小曲;是我脑际常常翱翔着的一只美丽灵鸟;是我青春之树上悄然飘失的片片绿叶;是我送给炎热尘世的一缕清风。
失败这东西是我的常客,我实在不喜欢与它为伍,可它就象我的影子一样,只到没有光照的时候,才偶然无可奈何地离开我一会儿。成功这家伙色彩斑斓,可她却象神秘的幽灵,老是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有时偶露笑靥,诱我追踪,但又总因脚力不健,而只能遥遥相望。我耐心地压抑着烦躁,忍受着失败的冷笑与它相周旋,是因为成功那美丽的笑靥给了我勇气和理智。
绘画实在是艰辛的。如今商海鼎沸,许多弄潮儿转眼之间即成“大款”,俨然尘世俊杰,而数十年也未必能造就出一个象样的画家,学画者浩如银河,成功者寥若晨星。欲走人生捷径,千万莫入此门。
绘画相对是寂寞的。一个三流通俗歌星能令痴情男女口颂心追,尽管他(她)的歌一转眼即烟消云散。而那些创造了传世之作的绘画大师也未必有多少人知道。不过自古圣贤多寂寞,这样相提并论就是可笑的,因此不必有什么感慨。
绘画本质是严肃的。决定其价值的唯一标准是品位。因此不必挖空心思地去制造最大或最小、最长或最短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更不必无端地以口代手,以脚代手或双管齐下制造作品,如果这不算杂技表演的话,只能是哗众取宠了。可怜的是新闻传媒却常常兴致勃勃地为之捧场,也是目前文化的一大悲哀吧。
绘画内涵是丰富的。在同一幅画前,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心境的读者会品出不同的滋味来。面对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教授和农夫的心理反应恐怕不大一样。
当然,我指的都是真正的绘画,不包括形形色色的假冒伪劣的东西,就像评说李逵时,绝对不包括也是手拎两把板斧,貌似英雄的李鬼一样。(李绍周)

Article
读 李 绍 周 诗 意 丹 青
柳江虹
早春二月,得《当代著名画家技法经典·李绍周诗意丹青》和《名家名画·李绍周》大小画集两册,于是,乙酉年的岁首,便沉浸在春的温馨、和谐与诗情画意之中。
李绍周是二炮政治部文艺创作室美术创作员,1985年在军艺深造时学习工笔画,1995年曾出版《李绍周工笔画》画集,一晃十年过去了,他的扛鼎之作终于又得以集中展示。如果说十年前,绍周的画册给炎热尘世送来一缕清风,那么十年后,他的人物丹青,又给繁闹人间平添一道清景,他的花鸟水墨,又给新朋老友带来一片清香。
读绍周笔下的人物,可以感受天地人和。无论是雪域高原的藏民,还是北方老农、傣家妇女,都是那样祥和、宁静、健康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饱满大气的构图,凝重抒情的色彩,严谨写实的造型,含蓄隽永的意境,不仅蕴涵了工写兼备的绘画技法,显示了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更传达出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经幡》中的藏族老人慈祥敦厚,神态笃定。丝毫不见曾经沧海、心如止水的伤感,全然是眼眸中的安详、发自内心的笑意。云在空中移动,经幡在风中飘动,唯老人不动,静静伫望,尽显桑榆之美。《斜阳》中的老妇,在自家的门前台阶上坐着,余晖的暖光托出她沧桑的脸,笑容里都是善良淳朴。《凤尾竹》中恬静的傣家女子,使人想起《诗经》的名句:“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想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的明净、纯洁、娴雅、美丽。绍周不靠突兀、怪诞之作哗众媚俗,却对传统的中和之美情有独钟。
读绍周的画可见含蓄之美。他的《花容》并没有渲染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颜,画面上的姑娘只是一个窈窕背影:她在执镜修饰,依稀可见落英缤纷,一瓣落在镜子上,让人不能不去想象那花容月貌和岁月无情的痕迹。《远方的云》也没有着力画云,依着牧栏的藏族男孩儿和他的妈妈,凝视着远方。远方有什么?也许眼中看到的是云,可是他们的心中一定在眺望远方的亲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古典美学思想对绍周的浸润可见一斑。
读绍周的画,还能品味诗、书、画兼得之美。绍周幼年攻学书法,文学早慧。他是在同学师长一致看好他的文才之时,转而步入画途的。不象现在许多孩子是考文化课吃力才去学画画。前人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品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绍周绘画,不能不说得力于他的文学和书法功底,以及他洁身自好,性情恬淡,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品格。运笔挥毫,兼得诗书画之妙;戎马从军,常念天地人之情。《名家名画. 李绍周》是一本花鸟集,将画家的主观精神和思想火花,自然地融入线条、水墨、色彩、图式之中,写成一帧帧雅致的小品,化作一幅幅情趣盎然的“春山”“秋波”。这些花鸟画,虽不见人,却可以感受人与自然的交流沟通,体察若即若离的生活气息。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人画和书卷气吧?绍周8月下旬将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再次举办个人画展,届时,他在绘画间隙自书的许多小诗,也将同时装成小框点缀其间,与满堂丹青相映成趣。
绍周在刚刚过去的本命年生日写诗云:“穿风过雨浑无痕,忽觉旅程已五分。苍鬓不谙红尘事,春风未老少年心。漫遣闲情读唐宋,偶将倦眼看烟云。凭谁一解无形锁,横涂竖抹尽天真。”他为横涂竖抹耗尽了一头秀发,难免喟叹“莫非昆仑千秋雪,万里飘到头上来。”我拿杜甫的诗句“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送他,因为他人未老,情正浓,诗意丹青的高峰还盼望着他不断攀登。
(2005年6月9日《火箭兵报》)

诗 意 入 丹 青
诗 意 入 丹 青
刘大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笔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众多优秀的工笔画家中,绍周以其含蓄隽永清新质朴的诗意丹青独树一帜,确立了在当代工笔画坛的地位。
绍周是在部队成长起来的画家,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便进入二炮政治部创作室,多年来不为时风所动,不为潮流所惑,勤勉而执著地从事工笔人物画的研究和探索,在中国工笔画的传承中不断地实践开拓,力求用传统的技法表现当代的题材,赋予这一古老画种以鲜活的表现力和全新的审美理念。以赤子之心去观照世界,体悟生命,在平凡无奇的生活中,深入开掘,发现瑰宝,激活灵感,倾注心血,提炼升华,创作了数量可观的精美作品,形成了自己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他的画面总是氤氲弥漫着清新醇厚宁静祥和的气息,不经意间就浸润和进入了读者的心灵,与你共鸣,使你感动,让你在庸常生活与平凡事物中品味出诗意内涵来。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中国工笔画正在走向新的辉煌。画家们除了创作题材的拓展外,在艺术理念、表现技法等方面也渐趋多元,丰富多彩。站在时代的高度,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富有个性的思想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我想只要能沉潜生活之渊,以平和的心态不断探求,就能走出自己的路来。绍周素来心性淡泊,步履扎实,我相信也祝愿他诗心永驻,激情不减,在自己开拓的诗意丹青之路上越走越好。
(该文为2005年8月中国美术馆《诗意丹青·李绍周近十年工笔画展》前言。《文艺报》、《中国美术》、《中华博览》、《中国美术馆》等报刊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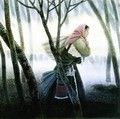
采 撷 心 灵 的 感 受
采 撷 心 灵 的 感 受
李绍周的诗画探寻
兰铁成
数年前,一个炎热的夏日里,绍周将刚刚出版的《李绍周工笔画》送给了我,前不久绍周又寄来了他新出版的两本工笔画册。我欣然翻阅着每一幅工笔画,先睹为快。清新的笔调、朴实的画风来自深山旷野的宁静,雪域高原的圣洁,还有敏感睿智的心灵。画中的一切,给炎热的尘世带来缕缕凉爽的清风。就这样,绍周的诗与画自然沟通了我们之间的军旅情结,是绿色军营,是战友,还是同道上的画友,相同的人生经历,把我们拉近了,丹青的领域里多了一个知音。
绍周五十年代出生在中原古都洛阳,家乡几千年深厚的传统文化,滋润着他的心灵,给他后来的工笔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要画出好画来不单纯是靠娴熟的技法,还必须要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绍周深知此道。他自幼酷爱文学和美术,和同龄人一样,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的洗礼,上山下乡的磨练,带着画笔走进绿色军营,青藏高原当兵八载,坚持学习和创作,快三十岁时进解放军艺术学院深造,大大地开阔了创作视野,丰富了艺术思维,毕业后任二炮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创作员,方才如鱼得水,创作自然有了新的转折和飞跃。
绍周的工笔人物画以青藏高原人文景观和军旅题材为创作主体,在青藏高原当兵的岁月里,对客观物象有了直观的认识和了解。那里的一切,与他心心相印,吸引着他,感染着他,自然萌发了清新质朴的审美取向,高原特有的原生态给他提供了艺术升华的客观条件。绍周与他人不同,用自己的审美视角观察物象,发现基础素材,概括性地提高和组合,再将他平时积累的文学素养作为形象上的语言基调,进行深入的塑造,以诗求画,以画含韵,追求自己的艺术境界。王维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知让多少诗人和画家豁然开窍,修成正果。《春之节》,两个战士扛着灯笼夹着鞭炮走在没膝深的雪中,一个老练沉稳,一个稚气憨厚,红艳的灯笼在寒冷单调的山林里闪耀着温暖,给守卫边陲的连队带来了春节的欢快气氛。《圣山》浓缩了青藏高原的人文景观。一个虔诚的老妇人,远望着心目中的圣山,一步一叩首,心灵深处许下美好的愿望,希望得到佛祖的恩赐,虔诚与天地合而为一。淡灰色的天空烘托着远方的灵光,黑白对比和谐,色调沉稳,老妇人衣服上的红与蓝,在整体色调上起到了调解平面空间作用,产生视角变化,雪花飘飘,佛光普照似有似无,营造了一种神秘感。笔法娴熟,渲染到位,构图简洁,给读者留下了范范无际的想象空间。《酥油茶》,滚烫浓郁的酥油茶,诱惑多少人心想往之。绍周在藏区普通的生活习俗中发现了酥油茶的创作视点,多次易稿,反复提炼,选择藏族少女为主体形象,红头巾,绿上衣,黑袍子,桔黄色腰带,跪坐着擦拭青花碗,面前有一把紫铜茶壶,一锅热气腾腾的奶茶。背景借鉴了中国画写意手法,进行意象渲染,随意性发挥,似有似无的墨韵,虚实有致,繁而不乱,与工致的人物形成和谐的对比,使人回味无穷。《晨雾》中,藏族母亲抱着孩子和一个年青女子站在草原高处,早晨的雾气从山坡下升腾弥漫而来,她们凝视的目光看到了远方的什么?《春锄》描绘初春的季节,两个藏族妇女专注地躬腰锄地,护理着幼苗,也护持着心中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满天风雪中,一对藏族夫妇正衣袂飞舞地走在《归途》上,巨大的白塔是他们眼中的景物,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皈依之所。《在远方》、《绿色小溪》、《风之声》、《尘梦》等等作品,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和精神内涵,艺术形式各有区别,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艺术魅力,这里不能一一诠释。
诗是绍周少年时就有的爱好,近年来写的多了起来,也是他工笔画创作的依托,是构思造境所需要的养分,“生来绿如玉,死去红似火,无意媚东风,来去皆本色。《题红叶》”写的是不卑不亢从容不迫的处世态度。“少年豪气依然在,双鬓不觉已半白。莫非昆仑千秋雪,万里飘到头上来?《忆青海》”字里行间充满了人生的感慨。“半俗半雅丹青事,非武非文尴尬人。如戏如梦名利场,不虚不妄平常心。《壬午岁末自况》”自我调侃中透出自信和对世事的洞察。平凡的花草,寻常的物象,在绍周的笔下随意勾勒渲染,有生命的视觉形象尽得笔墨,唤起读者对自然的想往,赤、橙、黄、绿、青、蓝、紫,都注入到绍周的“新工笔画”上。那悠然的天鹅,振翅的小鸟,飘落的红叶残荷,挺拔的新篁嫩草,屋顶上的几只南瓜,院墙上的一盆兰花,寻常巷陌中的一棵老树,残垣黄沙间的一弯新月,大自然的一切物象都是美好的,绍周为之情有所动,心有所思,听从心灵的感受,以变求新,以小见大,苦心经营,注重意境,画面处理颇有自家面貌,与他大量严谨厚重的工笔人物画相比,另有一番轻松隽永的味道。
如今画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名利而钻营奔波的画家比比皆是,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情况较为普遍。而绍周却像圣山脚下的虔诚行者,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执着求索了二十年,一步一个脚印,创作了一大批精美的工笔画。“一花一世界,一石一乾坤”,这是绍周常讲的一句话,可见他心中的艺术真谛是在没有被污染的“圣山”之中。他的作品沉静朴素,宏观而又具体,似乎游离于主题创作状态,绕过世俗常常关注的话题和主体视线,从平凡平淡的生活中撷取使他动心动情的灵感,再化作使别人动心动情的作品。绍周的工笔画,人物特征概括,形象简练而不失其精神,疏密关系恰当,主体突出而不孤立,构图构思严谨,意境含蓄而又深刻。多次渲染是工笔画完成整体构图的重要手段,绍周大胆借鉴现代重彩画,岩彩画,古代壁画和其它画种的色彩理念,强化了自己的色彩特点:厚重、艳丽、平稳、雅致、清新。他善于用环境衬托主体,画面物象的体积感自然有了主次,同时产生视觉中的三维空间,优美的画面展示了动人的诗画魅力。绍周工笔画的立意内涵和形式特色,综合体现了他丰富的艺术素养。
艺术需要发展,创造,与时俱进。年近半百的绍周兄,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积累了许多的创作经验。然而,对自己的创作,绍周总是谦虚谨慎,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继续坚持他的审美取向,同时不断学习和思考,使艺术观念不断得到扩展和更新。相信绍周还会走进新的生活原生态,穿越千里雪域,领略大千世界,采撷一草一木,追本朔源,发现新的视点,以画家对笔墨色彩的敏感和诗人情怀,去寻找新的突破。绍周的诗情画意会更加灿烂,新的丹青会飘然而至。
(2005年7月19日《文艺报》美术专刊)

工 笔 绘 清 风
工 笔 绘 清 风
彭俐
诗若可观真如画,画若能读亦如诗。
一册《李绍周工笔画》在手,一缕被月光染蓝的清风在握。人有人品,画有画格,品格为物,可知可感,不可言说。悬在不惑和天命之间的李绍周,正当艺术创作的盛年,但他“执一念而不改、秉一烛而不弃”的丹青劳作,已经是硕果累累。如果说作品多次在全国美术展览中获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还不能说明作为军旅画家的成就的话,那你就去读读他的画。
大多数画作,都是只能看的,只有少数作品可读。看,只需眼睛参与就够了;读,却要求眼睛、大脑与心灵三位一体地投入。画若可看已入流,唯有可读方为上乘。让我们先迈进李绍周的《门槛》吧。斑驳而厚重的黑漆大门,半开半掩,裹着黄裳的僧人,半嗔半笑。没有玄机的画面玄机自在,没有说破的禅意意味深长。被门槛淹没的是脚,被袈裟遮盖的是嘴角的笑,被遗忘的是大千世界的大千愿望。
那些在茫茫夜色里踏上《寒路》的人是谁?他们从哪儿来?又向哪儿去?寒冷的是天地,还是人心?从这些人本然的表情里,能读到无奈与执著,紫色的御寒衣显得凝重而沉静,人们急匆匆赶往的目标,也许是不需要早至的归宿。想到世事人生诸多的不期然而然、不可为而为之,面对《寒路》上的寒微人,不禁不寒而栗。
《长明灯》亮了,在古老的高原上。是鬓已斑白的老妪躬身用酥油把它点燃?还是一颗热得似炭火的心?那《长明灯》的火苗,是金黄金黄的,是迎春花一样的颜色,又像是水仙花一般的俏丽婀娜,曼舞在长夜里,犹如一万颗金星,会聚在一方屋檐下,为了一个传说中古老的期许,抑或是为了期许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不曾看见千万盏长明灯闪烁光芒的人,永远也不知道长明灯有多美、多亮。
《梦回故园》是另一番情调,褐色的黄土高坡,被梦中的蓝天和白窗棂拥抱,一对剪纸鸳鸯在相互亲吻,出生在古都洛阳、美髯公似的李绍周,对自己的故土、对家乡,竟然也有这般儿女情长。
是军人,就不能不画军旅生活。宋代诗人陆游诗中的“铁马冰河”,在他的笔下,被描写成雪国的美景,不见肃杀之气,惟有祥和之态。远远的,一名战士,挥手指挥着隆隆“铁马”过冰河,大自然的空旷与人物的渺小,对比成有情节的风景,别有韵味。
读《生存图解》(之一、之二、之三),则有另类的感觉,有哲思,有隐喻,也更有现代感在其中,笔法上细腻与粗犷并存,含蓄与奔放同在,是其风格多样、勇于探索的脚注。
诗意的追求,往往是画意的所在。在这一点上,李绍周颇得古人传承之妙。其它画,如《人在天涯》、《古桥图》、《秋色灿若霞》、《李清照诗意》、《苏东坡红梅诗意》等,都堪“吟咏”,作为专心研究工笔人物画的画家,他以画笔挥洒诗情,以诗心描绘苍生,怀着九死不悔的痴迷。
李绍周称自己的画,是“心田里流出的一支无名小曲”,是“送给炎热尘世的一缕清风”。其实,世上真正铭心的,常常是无名氏的无名之作。我们小时候被夜空中的几粒寒星所感动,兴奋莫名,并不在意他们是宇宙间太阳一样的恒星,还是月亮一样的卫星,也不再乎他们的名气大小。
(2002年6月16日《北京日报》)




























